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,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,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。” 近年来,在...
生源减少 没编制老师快开学才知道丢工作
摘要:
最近几年,随着出生率下降,教师群体中开始频繁讨论起“生源危机”。在一些地方,已经出现教师成批分流到其他单位,而与此同时,没有编制的临聘老师,受到的冲击往往更大。
比如今年7月,一位江西老师在问政平台上投诉自己被无故解约,当地教体局的回复很直接:“因人口减少,小学人数锐减,各小学不再续聘非编教师。”
类似的政策已不新鲜。去年,江苏如皋教育局发文,要求在“生源波动”的背景下,“让有限的编制充分发挥作用”,其中明确提出,“不得再新聘代课教师”。
还有许多地方,没有通知,但岗位的的确确消失了——许多临聘老师临近开学,才知道自己今年没了工作,急忙开始投简历。一些人失去的不仅是薪水,还有教师身份带来的体面。一个女孩至今没敢告诉父母,自己已经去了养老院做社工,“怕他们接受不了”。
文|王熙媛 周航
编辑|王一然
没有进群的人
直到秋季学期开学前两天,临聘教师杨帆才后知后觉,自己失去了工作。那天,她同校任教的男友被拉进新建的年级教师群,她却始终没有等到邀请。
后知后觉的,还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。去年,她带的两个班成绩都名列前茅,学校还特地把“火箭班”交给她。年级主任当面夸奖她:“明年一定要把你留下来。”
但潮水来临时,或许没有人能例外。那天,杨帆去问年级主任,为什么自己没有进群,对方回复:“我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,校长筛掉了,说不缺人。”
杨帆所在的学校建校不过三年,她在建校第二年入职,她记得当时临聘教师群里有一百多人;去年秋天只剩三十多个,直到上学期剩下不到十个;到今年夏天,人们互相打听:“你被拉群了吗?”答案都是“没有”。
严格来说,这称不上“清退”,而是不再续约。杨帆每年都要和学校重新签约,只签到六月。她觉得最“鸡贼”之处是,七八月不发工资,学校却照样给她缴社保,“怕开学还得用你”。
临聘老师,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代课老师,合同大多为期一到三年。在过去四年,南京的音乐老师果果换了四所学校,她称之为“流浪式任教”,“每年暑假都像抽盲盒,不知道下一站在哪。”
她签的合同也很不一样。有学校连合同都没签,每月打两千多块到她账户,才教了两个月,就说来了编制老师,不需要她了;有的合同只签到六月,这样可以省下暑假的薪资。
果果最喜欢那所签约一整年的学校。在那里,她有绩效、有奖金,有和编制教师一样上公开课的机会,学校发生活用品、水果券、蛋糕券,也都有她一份,“真的给人一种错觉,我会在这所学校干到退休”。
直到今年教师大会前夕,她接到通知,学校来了有编制的老师,不会再聘请她。而这个时间点,意味着她错过老师招聘的高峰期,她气得索性离开南京,回到了老家广东。
展开全文
图源东方IC
这样的群体,在制度上是被允许存在的。教育部2011年的文件规定:因教师进修、产假、病假或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等导致临时缺员,难以调剂的学校“可以临时聘用教师”。
但现实往往比政策更复杂。财政吃紧等原因下,不少地方变得更依赖这支“临时”队伍。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》显示,2019年全国临聘教师达到37.83万,比2011年多了近10万。有学者调查发现,一些地方“有编不补”和大量雇佣临聘老师同时存在。出生率下滑的背景下,一些地方也更“巧妙使用”临聘教师——有学者指出,为避免将来超编,部分地区选择“技术性预留”编制。换句话说,许多人在入校的那一刻起,就注定只是被暂时需要的那群人。
杨帆也明白自己失业的原因。她老家江苏某县,近几年乡镇人口减少,其中四所初中被直接撤并。有编制的老师调到城区,去年还属于她的岗位自然换人了。
同样在今年暑假,江西女孩素素也结束了自己的教师生涯。原因是相似的:有编制的小学老师过剩,调入幼儿园,挤掉了她的位置。
初中毕业那年,素素就决定做一名幼师。她参加了当地定向培养项目,读五年书,拿到大专文凭后回家乡幼儿园。那是2019年,她大学毕业,通过县教育局考试,成了一名“区聘老师”,和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签约,为期三年。
她记得刚工作那年,镇上的幼儿园老师还是没幼师证的“临时工”。她入职那年起,连续几年招区聘老师,才逐渐补齐“两教一保”——每班两名幼师、一名保育员。全园三十多个老师,除了七八个有编制,其余都是区聘。
这几年,她眼看着学生一年比一年少。刚上班时,镇上还有四所村级幼儿园,今年最后一家也关门了,学生都集中到中心幼儿园,人数仍不及当年。幼师群体里,最先被淘汰的是没证的“临时工”,今年终于轮到她们这批“区聘老师”。先是1月,四位老师合同到期被告知不续签;7月,包括她在内的五人等来同样的通知。
素素说,园长也很焦虑,说她们对幼儿园很重要,还曾和上级沟通,但是最后回复的消息是,“根本就没有位置”。
“我们确实是幼儿园的主心骨,有当后勤主任、保教主任的,有当班主任的。”电话里,素素止不住叹气,“可上级领导不管这些,他只看人数。”
大家很快接受了解约的现实,“都知道工作反正没有了,也没有什么挽回的地步了”。能争取的只有赔偿金。素素拿到了六个月工资,以补偿她过去六年的付出。
杨帆则连赔偿都没敢争取。男友还在学校,她怕给他惹麻烦。得知失业的那天,她一晚没睡,只是默默刷社交平台、招聘网站和人才交流群,为自己寻找下一站。
脆弱的体面
这次向我们讲述的临聘老师都是女性,这并非偶然。有学者2019年在华北某县调研乡村临聘老师情况,受调查的486位老师中,女性有479人,平均年龄34.3岁。
教师行业女性居多,临聘老师更是如此。另有学者在2020年调研了12个省份36个县的教师数据,在编老师中,女性占比62.19%,而编外的临聘教师中,这一比例抬高至84.47%。
说起为什么做临聘老师,杨帆、果果、素素的答案几乎是彼此的复制粘贴,“父母觉得女生就应该做老师”“世俗眼光觉得,(老师)是一个对于女孩子体面好嫁人的工作”。
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,杨帆也曾试图走自己的路。她在南京一家传媒公司做直播运营。下午两点上班,深夜十二点下班。那份工作节奏快、压力大,但薪资尚可:她作为新人,底薪有六千,算上合作主播提成有八千。
更吸引她的是这份工作的前景,公司旗下有很多百万粉丝主播,负责人欣赏她,没多久就把转正提上日程。但她在县城生活的父母,坚决不同意她“在外面瞎折腾”。她记得刚干半个月,端午节回家,爸妈就说赶紧收拾回来。她回了南京,爸妈每天来一通电话,“一直要我回家”。
杨帆最后还是顺从了。她回到家,听从父母建议考公,但在80:1和120:1的报录比现实中败下阵来。后来,父母托亲戚关系,把她介绍进县城的初中做临聘老师。
杨帆经常觉得,相比自己,父母更需要这份听起来体面的工作。她成了父母口中“在某某学校当老师的人”。不过,“他们从来不会提临聘这两个字。”她说。
她基本月工资三千,比男友少近两千。另外,她没有公积金。但算上奖金、各种补贴,一个月平摊下来六七千收入,她其实也挺满足。
为了保住这份工作,她比其他人更花心思教学:她发明积分制的“免抄卡”鼓励学生举手回答问题,还精挑细选了四个课代表,给吃给喝,让他们帮忙监督纪律。
图源东方IC
杨帆的努力也不仅仅为了维持这份脆弱的体面,她也在乎“作为老师的价值”。她常年贫血、低血压,头一年做班主任,累得好几次差点晕倒在办公室,学生成绩没那么理想,她觉得很挫败。第二年,为了“再次认可我自己”,她辞掉班主任,更专注教学,所带的班级月考一直第一第二。这份成绩让她即使失去工作,“也没有很失望伤心,因为至少也证明过自己。”
她有时也会羡慕男友的松弛感,有次对他说,“你(的班)哪怕考十次倒数第一,领导也不能把你辞了。我(的班)要是考两次,领导就说这老师不行,明年不要了。”
家庭餐桌上,男友经常被拿来当作让她考编的正面典型。但杨帆在家乡根本没法考。她学的是财会专业,而教育局招聘都要求师范类专业。只有少部分岗位不限专业,但要求硕士学历,她也只有本科学历。当年她也打算过考研,书都买好了。但和父母的一次长谈改变了她的想法:家里条件一般,弟弟还在读初中,读研需要学费和生活费,财务专业的费用还更贵。就这样放弃了。
在体制里,编制永远是条清晰的分界线。和在编老师相比,临聘老师基本工资和五险一金有着显著差距。福利也有差别,大到过节费,小到体检,她们经常发现自己被忽视了。
在宁波某小学,音乐老师陈可欣享受到的公平待遇是能收到同样的节假日礼品,但又没公平到能参加年度体检;教育局组织旅游,编制老师能报3000元档的,她只能报1500元档的。
陈可欣也知道,自己随时都可能失去工作,她选择主动疏远人群。开全体教职工大会,别的老师在一起有说有笑,她只低着头玩手机。
就连考编,工作三年的她也已经“摆烂了”。她毕业于综合性大学音乐师范专业,和专业的音乐学校有差距。而当地音乐老师的统考招录比例大概是100:1,和更年轻的毕业生一起竞争,她已经不抱希望。
老师莫莫同样讨厌自己在学校的处境。每年都有人问她,“你报名了吗?”“考上了没?”在这里,在编老师默认代课老师一直要考编,“默认你会一直考到35岁”。
莫莫很坦率,说这份工作是父母走关系安排的。在江苏某座小城市,她觉得身边临聘老师有一些共同之处:家里经济尚可,家长看重学校的社交环境,“毕竟有的职业碰到的同事层次比较低。”
但真进到学校,她觉得这工作根本不像社会上说的那么轻松。领导经常让她做杂活,还安排无薪帮上课,“美名其曰锻炼能力”。她觉得这也和临聘老师身份有关:年轻、怕失去工作、普遍比较听话,领导更愿意使唤。
但她不一样,“我觉得我拿2000多,没有必要干一万的活吧”。有次,领导找她做PPT,她以太忙为由拒绝了。之后领导把聊天记录发给她父母告状,“说我太懒,不懂得职场人情世故,连领导都敢拒绝。”
在学校,她也能感受到老教师们语言的不屑。有次他们讨论学校活动,她凑过去,想一块听下,他们说,“这个跟你没关系,这是体制内的事”。
这份传说中好找对象的工作,却让她自己相亲时没有底气。介绍完自己工作,总要补充,“我会继续考试的”“我是个上进的人”。说这些话的时候,她说“自己都感到脸红”。
只待了一年,在经历一个暑假的思考后,莫莫决定离开,开学前领导问要不要来上课,她说不去了。
围城内外
莫莫说,她害怕像学校里那些30多岁的临聘老师,结婚有了孩子,更陷入这泥潭中。“代课老师就是温水煮青蛙,拖得越久,越难找工作”,她觉得所谓体面,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话语,“大部分当代课的人不可能就这么甘心一直待下去,他们心里肯定是很挣扎的,只不过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安慰自己吧。”
刚开始,父母埋怨她裸辞,但她找到现在这份薪资翻了几倍的工作后,他们也不说什么了。她觉得自己有了真正的“尊严”,再去相亲,“很有底气说出自己的工作”。
但干了六年幼师,失去工作两个月后,素素还是怀念着幼儿园的工作。下班走着就能回家,晚上还有时间打球,到了周末,能约朋友出去玩。她老家有景区,家里开了民宿,忙的时候,还能帮帮忙。她觉得已经过上了想要的生活。
当地工作机会也很有限。最近,她看到县里其他镇有私立幼儿园在招老师,月薪两千多,她还犹豫要不要去面试。身边朋友都不理解她,“说去厂里打工都能有五千块”。
她自己想想也觉得好像不值当。她现在领着失业金,都有1500元,而且她也不知道那座幼儿园能维系多久。
也许也是自己太追求安逸了,但她确实也不想跟着父母做民宿。那样太累了,几乎全年无休。何况她还有个弟弟,“民宿以后肯定是他的吧,因为女孩是要嫁人的”。
处处是围城。当一些人离开,一些人被驱逐,还有许多人在挤破脑袋,求一份临聘老师的工作。
在广东一个地级市,这学期应聘时,陈晓玲看到一张面试签到表上的竞争更激烈了:应聘者不乏教龄5年、8年,甚至10年以上的,有重点大学本科,也有研究生。
这个2001年出生的女孩,社交媒体签名是长长的句子:“一直在努力的师范生,一直在奋斗的师范生,一直在期待上岸的师范生”。
过去的三四年,陈晓玲已经考了十次编,她觉得临聘教师的工作至少让她不用脱产备考。为了更好地准备教师编的面试,她离开此前教学要求不高的原学校,去往区里更好的学校,希望借此锻炼面试能力。像追逐一趟末班车,她觉得考上了,也不用再担心生源减少,“就算调岗了也还是会有你的位置”。
图源东方IC
转行总是需要更多勇气的。从南京换了四份临聘老师工作后,回到广州的果果走出了第一步,在一家公司做电商文员。收入比不上做老师,单休,但她想给简历增添点不一样的内容。
“我想通过我的转型告诉大家,你的人生除了当老师还可以干很多事情,不要被所谓的‘体面’世俗的眼光给束缚,趁年轻,赶紧逃离这份‘夕阳产业’。”果果说。
但其实果果也很纠结,要不要再做回音乐老师。她很怀念待在讲台的日子,学生们也喜欢她,会围着她,下课了和她打招呼。她最新的帖子记录了自己工作的点滴,像是一篇对过去生活的讣文,“那种被需要、被信任的满足感,谁懂啊! ”
失去工作后,杨帆第一时间也想再找一份临聘老师工作,但时间太晚了,所有缺口都补上了。
她来到县城里最大的教培机构。面试时,负责人说:“我们这里是正规机构,以教学为主”。但正式上班,她头天就被告知,“老师们,今天我们的电话KPI是160个”。
事实上,只有周末安排了一节课,她其余时间全在公司打电话招生,每个电话要填表、拍照,还被家长频繁质问“你们哪来的电话号码?”只干了三天,工资都没要她就跑了。
刚失业的时候,杨帆有一种强烈的冲动,想要离开县城,去更大的城市。但感情让她留了下来——在县城,她说除了体制,最高薪的工作就是进厂或销售。她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12个小时不停在纺织厂拉布,再者,“我觉得自己还没到需要去做体力活的地步。”
在求职网站看了一圈后,她决定到小区10分钟路程外的一家养老院做社工。单休,每个月三千多,比她看的其他工作薪资低,但她看中这是个朝阳行业,没准还能发展做自媒体。
养老院和原来的学校在一条街上,她很快感受到了尴尬。小区里认识的邻居在养老院看到她,“你怎么来这了?”“你不是做老师的吗?”一传十,十传百,很多人都知道了她去了养老院。大家也不知道社工干嘛的,她听说自己在别人口中,变成养老院前台了,“虽然社工也没什么含金量”。
她心里清楚,自己也没有完全跨过内心的阻碍,“面子上确实有点挂不住”。有次在养老院,她碰到认识的快递员,他们各自瞄了对方一眼,她帮对方叫完取件人后,立马逃跑似地走开了。她担心别人以为她之前说自己当老师的事情是在撒谎。
让她困扰的还有,这件事要怎么告诉父母。中秋节,她照例给父母送礼物,但自己没敢去,让男友代劳了。她没让男友吐露她现在的工作,“他们可能会很难接受”。
(文中讲述者为化名)
相关文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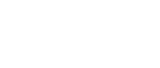







发表评论